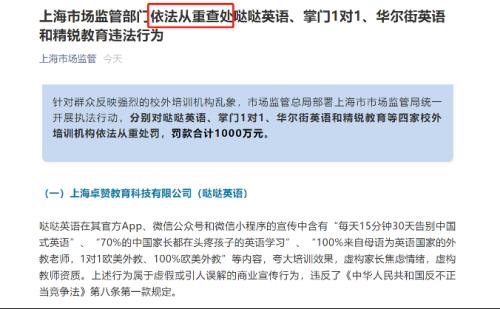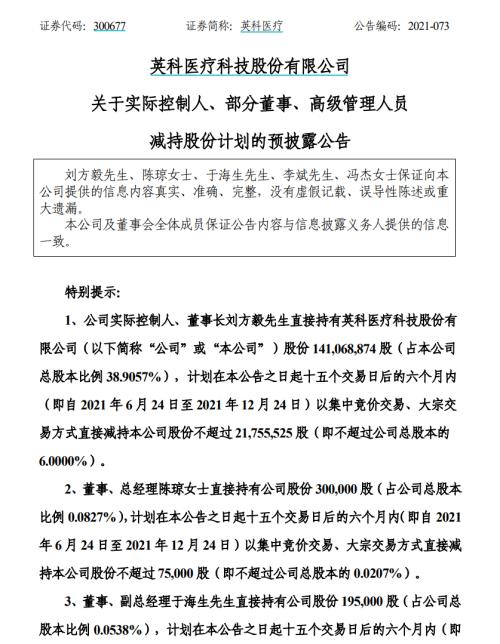自闭症孩子的儿童节,快乐还是绝望?丨儿童节专题
来源:蓝鲸财经 2021-06-02 10:24:13
儿童节,大部分孩子可以在节日礼物和惊喜中感受到快乐。但也有一部分孩子,对这一切都毫无兴趣。
他们被称为“星星的孩子”,患有自闭症。由于兴趣局限等临床表现,他们很少对外界的刺激显示兴趣,甚至有一部分自闭症儿童没有情感需求。他们所在的家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家庭的愿望很简单,只是希望孩子在未来能够生活自理,可以有一份工作谋生。
然而,对这些家庭而言,如此简单的愿望,亦如此奢侈。
奢侈的愿望
希望他最终能生活自理
为了给小辛进行更好的康复干预,小辛妈妈和小辛奶奶从南京来到北京有一年多了。原本以为来康复干预一年,孩子就可以回到南京正常上幼儿园了。没想到,小辛的康复干预之路还远未结束。
小辛今年5岁了,正常情况下是上幼儿园大班的年级,但小辛没办法正常上学,目前全部的白天时间都在北大医疗脑健康进行密集干预。
小辛妈妈是在小辛三岁半左右发现孩子发育迟缓的——最开始小辛还有语言,到三岁之后原来会的语言慢慢不会说了,语言越来越少了。小辛父母带着小辛在南京当地看了几家医院又去上海挂了专家号,“所有的评估都做下来了之后,医生也没有确诊,只是倾向于打个问号,但建议我们要密集干预。”
在南京找机构干预了几个月发现成效不明显,就决定到北京找更专业的康复机构进行干预。“从前我们从来没有关注过自闭症,突然一下子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那段时间,晚上觉都睡不着,你看我白头发特别多,愁的。”小辛妈妈说。“我的孩子还有两个月就5岁了,我每次坐在机构外边看到那些两三岁的孩子就会特别羡慕,有的家长还会和我说孩子干预了多久效果太慢了等等。其实我的心里很崩溃,我就在想,人家孩子两三岁都已经急成那样了,我的孩子要比他们大很多,我的孩子要怎么办啊。”(自闭症儿童干预的黄金期在2-6岁之间,越早干预越好)
现在小辛经过机构密集干预已经有了一些语言,可以简单发音,也有一些基本的认知,但还没有主动语言。小辛妈妈原以为孩子经过一年的干预,就可以回到南京进入正常的幼儿园或小学,但现在她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现在我已经不去看那些普校了,我会看一些水平高一点的特殊教育学校。以前我会希望他去上小学,然后再上个初中,但我现在只希望他最终能生活自理。小学学的东西又难又多,而且普通学校学的东西咱们平常生活大中不一定能用得上,我儿子本身就学东西慢。我就在想,以后他学点能用得上的,能帮助他生活自理的就可以了。”
能够生活自理。这是小辛妈妈对小辛最大的期待,“以后他能找到一份最基本的工作,哪怕是去工地搬砖,他能够知道搬砖的流程是怎样的,能够把这份工作坚持做下来,我就觉得很了不起了。”
希望他能进入正规的教育轨道
相较小辛,壮壮的情况要好一些。壮壮每天上午去住所附近的普通幼儿园,下午到机构进行干预。幼儿园的校长和班主任知道孩子的情况,给了壮壮一定的包容度。
目前,壮壮爸爸放弃了央企单位技术研发的工作,全职带壮壮。他偶尔会因为壮壮取得的一点进步,和壮壮妈妈、奶奶像过节一样开心。也会陷入一种焦虑到接近崩溃的状态。
“我从来不会再家里表现出很悲观的状态,但能体会到情绪慢慢累积的崩溃。我经常会有焦虑到失眠的状态,或者突然在两三点就醒了。有一段时间老做梦,梦里都是小孩,我带我的孩子出去玩,我的孩子突然做了些奇怪的动作或者行为,当时的气氛特别尴尬。然后我突然就醒了。
“白天我们就想着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给孩子,包括回家已经特别累了,也要喝点咖啡陪孩子继续玩,因为专家说了,不要让孩子闲着,家长要一直陪着他,我们不能松懈。以前我和孩子妈妈还可以抽出点时间去看个电影,现在不可能的。每天都在这种高压的状态里。没有说一下子崩溃了,但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压力压着你,没有时间透气。”
壮壮爸爸最怕的是带着孩子出去玩,孩子突然出现一些奇怪行为,比如抓别的小朋友一下或者是突然抱住别人,“小朋友家长就会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就会觉得这孩子肯定是父母没有教育好。这个时候觉得自己还挺委屈的。”
目前壮壮在读普通幼儿园,但普通幼儿园的老师对特殊教育的认知不多,更别提能够提供更符合孩子需求的教学帮助。壮壮爸爸想给孩子找一家融合幼儿园,但在住所方圆15公里之内都没有找到,所以现在只能维持现状。“现在的融合幼儿园真的太少了。”
他很希望幼儿园或者上一级单位能够为幼师做一些基本的特殊教育培训或讲座,比如ABA(应用行为分析)如何强化,当孩子发生一些问题时如何更好地引导孩子。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以后能够进入到普通教育中,那么上小学之前的幼儿园阶段太关键了,这直接决定着我们能不能融合进去,但目前的幼儿园,对于我们这样的孩子来说,中间好像有一个空白地带。”
困局
融合教育依然艰难,制度和法规尚存漏洞
壮壮爸爸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个群体共同面临的困境——尽管国家给予了诸多政策支持,但实现融合教育依然艰难。
机构康复干预之后,学龄儿童势必要融入到正常的学校环境中,但家长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学校可能以各种理由拒绝这些孩子入学。第二个问题是,即使学校接受了这些孩子,但没有合适的能够随班的影子老师帮助孩子从机构到普校过渡,他们也很难在班级里待得长久。北大医疗脑健康行为发展研究院研究专家周雅文表示。
在中国,可以把影子老师定义为特教助理——进入幼儿园、普通学校,为特殊儿童提供个别化教育支持,包括协助教师向特殊儿童提供教学计划和其他直接任务,记录并报告特殊儿童的进度。这个职业在国内刚刚兴起,还没有一套完善的培养制度,从业人员依然稀少。同时,国家并没有通用的资质认证和考核方式,行业里鱼龙混杂,培训三天就上岗的也大有人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聘请一位影子老师每个月的费用大概上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大部分残障儿童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随”就大多等于“混”,教师对这些孩子的学习基本都只能放任自流。家长只看重孩子在普通学校而不是特殊学校上学,不被贴标签,对孩子学习成绩、个人发展并不看重。
由于我国的教育实情,大部分学校,包括二线、三线城市,一般教师不具备实施特殊教育的能力,这就很难让教师充分认识到特殊儿童个体差异,无法进行定制教育,更无法给予这些孩子充分的理解与权益保障。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市还尚未建立针对融合教育的指导中心或研究中心,而且融合教育的监督机制、评价机制也没有得到有效建设。
融合教育发展困境的根源主要还是制度保障和法律法规方面存在不足,尚需完善提高。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发展平等、优质教育,但拒收特殊儿童进入普通学校学习的现象在部分地区还时有发生。另外,政策重点似乎仍然集中在义务教育和就业安置上,对于患者实现自立自强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学前阶段,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有效的投入。
康复机构稀缺,资源分布不均
根据中国残联官网数据,截止2019年底,我国共有残疾人康复机构近万家,其中,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占比仅1/5。
康复机构的数量远远难以满足患病率日益上升的自闭症儿童群体。据2019年发布的《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Ⅲ》,中国自闭症发病率达0.7%-1.0%,全国约有超1400万名自闭症谱系障碍人群。
康复领域方面,这些康复机构所覆盖的康复领域仍是基于应用行为分析(ABA)的自闭症干预为主,随后分别是言语语言治疗领域和感觉统合训练。儿童康复机构开展的服务主要还是针对小龄儿童,为大龄儿童提供康复教育和职业教育服务的康复机构十分稀缺。
总体而言,我国儿童康复机构以民办为主,呈多方主体共存景象。同时,以服务2-8岁小龄儿童为主,大龄儿童康复服务相对稀缺;疾病类别上以自闭症康复为主,言语治疗与感统训练并资源分布不均、头部机构稀缺,是行业发展的一大问题。《2020年度儿童发展障碍康复行业报告》显示,除北京外,我国优质康复资源、康复机构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及珠三角地区,而西藏、青海、宁夏等中西部地区的康复机构则较少。
由于儿童康复机构数量少且专业能力不足,二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儿童康复供需严重不平衡,满足不了广大障碍儿童(包含自闭症)家庭的基本康复需求。因此,为获得专业的康复干预,许多家庭就如上文提到的小辛家那样,只能带着孩子跨城市、跨地区进行康复治疗,大大增加了家庭的负担。
从机构体量上来看,儿童康复机构以单店运营的中小型机构为主;大型连锁机构占比较少。2021年,体量相对较小的单店机构和个人工作室,如何快速建立专业的康复体系、找到可持续的经营之道将成为成败关键。
专业师资不足,缺少行业标准
“师资团队”和“教学专业性”是机构发展离不开的两大核心关键词。
北大医疗脑健康儿童发展中心富华中心校长李毅表示,老师的专业水平是康复机构的生存根本,但目前康复行业的从业人员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跟不上需求。“目前国内高校没有成体系的培养机制,比如目前无论是医学还是教育学的院校都没有开设康复专业,或者更多的是偏成人康复,缺少儿童康复这领域的专业。”
一方面是大众对这个行业和专业的了解很少,学习特教专业康复专业的人又很少。另一方面,行业还没有展示给他们好的职业成长路径和规范化的培养体系。北大医疗脑健康行为发展研究院研发专家吉宁对此做出分析。
目前市面上大中型机构都有自己专门针对康复师的训练体系,也会推出一些面向全国所有康复师的专业课程,虽然北大医疗脑健康也在推动这件事,但从国家层面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些康复师也没有国家认证的证书可以考取,教师资格证其实对康复专业来说用处又不大。
破局
推动行业标准,建立师资培养体系
目前北大医疗脑健康正在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国家孤独症康复研究中心做康复师从业上岗培训,“我们希望把入门的标准建立起来。”吉宁表示。
另外,北大医疗脑健康也在推动医教融合。“从事特殊儿童教育相关的工作,整体上可以定位叫康复教育专业,这也符合国家教育部特教处一直强调的‘医教融合’概念——这是特殊教育中最核心的指引性理念。这些孩子需要医疗和教育共同去发挥作用,单独的教育解决不了问题,单独的医疗也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意识到要展开康复教育方面的专业。北大医疗脑健康也在和相关专业院校签订战略协议,去帮他们搭建康复教育专业方面的人才培养体系。从中专大专里开始培养相关的人才。”
另外,北大医疗脑健康行为发展教研院在相关高校推出了A-PKU校园杯儿童康复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我们通过大赛的形式给他出考题,给他出教材,先让他学习、看案例,再让他自己去体验某一个技能应该怎么教。让大家有一个感受,你未来是要面对这样的儿童,不管你在普校工作,还是想在我们这样的机构工作,还是在医疗系统工作,你都会遇到并要帮助这些特殊需要的儿童,你需要做的事情可能和你书里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最后,北大医疗还做了一套A-PKU儿童康复人才培训体系。“我们参照国际上比较认同的一套ABA的专家认证培训体系,今年北京大学医学继续教育学院申请下来课程资格,帮助这些康复师考 BCBA和BCaBA的证书,实现了一个专家水平从业人员的教育和考证的问题。”
从前端扩大人才储备和建立培养体系,到让更多人了解行业,到拿到上岗证书,再到工作后端建立起进阶培训标准,这样整个行业会慢慢进入有标准的阶段,跟上接近5000万所有特殊儿童的康复干预需求。
点点星光
事实上,特殊教育领域已取得了很多进展和成效。
从政策落实端来看,我国融合教育获得了巨大成效。《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普通小学、初中在校生30.40万人,其中有残障儿童5.66万人。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或在附设特教班上课的残障儿童,占我国特殊教育招生总数的51%。
从诊断端来看,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孩子的发育健康问题,自闭症等病情也越来越早地被诊断——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科学表明,自闭症儿童的康复干预黄金期在2-6岁,越早诊断出孩子存在发育异常,越能为孩子赢得更多的康复干预时间。
吉宁表示,“之前我们一直说自闭症的早期诊断太晚了,所以近两年全民总动员地把儿童自闭症等早期筛查加入到整个妇幼保健体系的体检筛查中。”带来的结果是,我们的调研数据提示孩子平均3岁左右发现其存在发育异常,而国外是4岁。“我们可以比美国更早地发现这些发育异常的孩子,这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成果。”
周雅文通过自己切身的观察和体会也发现了,国内特殊教育行业的发展速度并不慢。
“这个行业是在日日向好的。”周雅文提到自己一个很深的体会是,“我曾在美国工作过,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同事聊起来,他们会说在他们国家找不到可以聊ABA的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国家在这个行业发展并不慢。
“另外,我在8年前刚从事这个行业时,国内专业的康复领域非常安静,听不到什么相关的声音,也不知道有哪个地方可以给这些孩子做干预,但这几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各类专业的大型机构,还有专业平台已经非常多了。”
什么叫做“正常”?
采访结尾,周雅文说,她希望大众对自闭症等特殊儿童也能像国外那样包容,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自闭症并且接受这个群体。
吉宁说,虽然自闭症终身不可治愈,但通过干预提高生活能力,能够实现生活自理,找到一份工作,甚至可能成家立业,这个比例可以占到一半左右。虽然他们没有脱离自闭症的诊断结果,他们可能有一些社交问题,他们和别人格格不入,但周围人都很包容他,最后他也可以很好地生存。
由此可见,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包容程度也将决定他们未来能否独立生活下去。
一位记者曾在采访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杜亚松时问他:“自闭症患者有一天能否变得正常?”他反问道:“什么叫作正常?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是正常的?谁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这样那样的缺陷?”
想来,这个世界莫不如此。正是因为那些“不完美、不正常”,这个世界才更具多样性、才更多姿多彩。